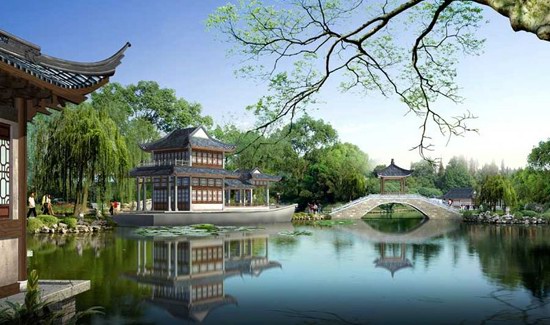秦军功爵制还规定,根据爵位高低,可享受不同标准的“传食”待遇。秦代官吏出差,都要住在官办的传舍(招待所)里。传舍对于住宿的各级官吏及其随员,根据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,供应不同标准的伙食。这个规定当时叫做“传食律”。
总之,商鞅的变法措施,具有系统性;内容细致周密,具有可操作性;商鞅身亡后仍然能推行下去,说明它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,具有持久性。
东西方变法比较
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希腊城邦改革,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商鞅改革的实质。雅典城邦从梭伦(约前640-约前558)到伯利克里(约前495-前429)的改革,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,鼓励工商业发展。商鞅变法则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,战争动员能力,促进农业发展。
同样是打破贵族血统,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财富划分社会等级,商鞅的二十等爵则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。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,后者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。
梭伦改革中,与财产定等级原则相配合的,是各等级公民政治权利的差异。例如,第一等级(第一等级称“五百麦斗级”,年收入(含谷物、油、酒等)总计在500斗麦以上。)可任执政官、司库及其他公职。第二等级(第二级叫骑士级,年收入300麦斗以上者。)可以担任司库以外的所有公职,说明管财税的司库官有更高的个人财产要求。与第三等级不可做高级职位,尚可担任一般公职不同,第四等级一般不担任公职,最多充当陪审员。(第三等级叫“牛轭级”,年收入200麦斗以上,大约属于有牛耕田的农民;第四等级叫“日庸级”,收入不及200麦斗,靠出卖庸工为生,故称“日庸”。)
商鞅改革之后,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,如张仪、范雎、蔡泽、吕不韦、李斯,不知凡几,平民通向政治道路,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。但非贵族化和平民化的政治,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,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,社会的过度平面化,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,才能阻遏混乱,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。相反,公民政治中的等级制度,倒使秩序规则的维护和统治权力的制约,具有现实的操作基础。
如何看待这种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呢?
一是产业的差别,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、兼及畜牧业的国家,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、工商立国。因此,各自对于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,激励重点不同。
二是民众与人口的差别,内陆秦国的百姓,父祖相传,安土重迁;而雅典的居民,则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移民。公元前500年,持续增长的雅典人口,成年男性公民仅3万多人。秦国人口大约有400-500万之多。诚如孟德斯鸠所言,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;人口众多则多实行君主制。(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还认为,希腊罗马的市民奴隶,与亚洲的政治奴隶(即庶民)不同,从而影响其政治制度。这也具有一定启发性。比如,雅典公民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,既是政治主体,又是政治客体;公民之外,有百分之九十的奴隶,只是工具性奴隶,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。少数公民之间的民主政治有现实操作性。秦国虽然只有贵族官僚才是政治的主体,但是,庶民依然是政治的客体,参与了政治的过程。君主反而凌驾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上。)
文艺复兴,将古希腊的传统接续为西方的政治制度。“百代皆行秦政制”——商鞅变法为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调,甚至影响到今日社会与人心。
本网站整理 资料来源:凤凰国学 作者:张国刚
[点击查看] 加拿大房市:大多伦多及周边地区房屋成交价格查询: